Palantir 執行長新書!《科技共和國》首度揭開矽谷另類的管理哲學
有一家科技公司走出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它拒絕為中國和俄羅斯提供服務,明確表達政治立場。
它花了 17 年才上市,遠遠超過同時期的 Google 和 Facebook。它的執行長擁有哲學博士學位,師從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還是太極大師。
這家公司就是 Palantir,一個以《魔戒》中的「真知晶球」(Palantír)命名的軟體巨頭。
在今年二月他們的執行長 Alex Karp 和 Palantir 企業事務主管的 Nicholas Zamiska 合著《科技共和國》一書。
這也是首度由內部人士第一手分享,Palantir 如何建立獨特文化、工作準則,尤其背後的假設和思考脈絡等。
他們也試圖透過整本書的篇幅回答為什麼 Palantir 選擇如此特立獨行的道路?它的反主流哲學如何幫助公司在 20 年間,從爭議新創成長到市值千億的帝國?
最重要的是,它正在進行的重建科技共和國實驗,對整個科技產業意味著什麼?
這期內容會有:
Palantir 的起源故事:延攬哲學背景的 Karp 加入
《科技共和國》這本書在談什麼?
1. 反主流的價值觀:「我們不是矽谷的一部分」
2. 深入泥濘、貼近問題核心
3. 避免淪為顧問公司:碎石路、高速公路
4. 對抗從眾壓力、建立建設性的不服從文化🔒
5. 借鏡蜂群組織學:去中心化的協作模式🔒
6. 即興戲劇哲學:擁抱不確定性與靈活性🔒
7. 重建科技共和國,跳進創新沙漠中🔒
8.建立所有權、Skin in the game🔒
9. 長期主義:超越季度報告的視野🔒
結論:必須自己發明第三十六房🔒
喜歡這期的內容,歡迎分享給朋友一起訂閱《VK 科技閱讀時間》,祝你今天一切順利~
Palantir 的起源故事:延攬哲學背景的 Karp 加入
這裡還是快速介紹一下 Palantir 的起源故事,如果你對他們有更多興趣,也歡迎參考之前的文章。
Palantir 的名字來自托爾金《魔戒》中的「真知晶球」(Palantír),象徵著從海量數據中洞察真相的能力。
這裡可以稍稍岔題,只要跟 Peter Thiel 有關的公司,幾乎都會用《魔戒》中出現的字來命名公司。
一直不知道背後用意,直到看了一篇他在 2007 年的訪談:「在聖馬特奧高中,Thiel 閱讀了 J.R.R. Tolkien 的《魔戒》,這本書一直伴隨著他。Thiel 說,他被 Tolkien 關於中土世界的故事所提出的關於權力的使用和濫用的問題所吸引。」
Palantir 的誕生和一場改變世界的恐怖攻擊密切相關。
過去在 PayPal 用來檢測網路詐騙的演算法「IGOR」,可以把它想作防範網路詐騙的數據分析技術,後來也引起了 FBI 的興趣。
2001 年 911 事件後,PayPal 共同創辦人 Peter Thiel 開始思考一個問題,這時他在想有沒有辦法把這套數據分析技術,應用在更廣泛的領域,像是識別和跟蹤對國家安全的潛在威脅。
2003 年,他找來史丹佛畢業的 Joe Lonsdale (他現在是 8VC 共同創辦人)和 Stephen Cohen,還有 PayPal 工程師 Nathan Gettings,開始打造 Palantir 的原型。他們只用了八週時間就完成初版產品。
但這艘名為 Palantir 的船,還缺一位掌舵的人。
Thiel 面試各種有執行長經驗的候選人,但都不符合他的預期。最終卻選擇一個完全意想不到的人選:他在史丹佛法學院的同學 Alex Karp。
這個決定看起來很奇怪。Karp 沒有技術背景,沒有當 CEO 的經驗,也不熟悉政府業務。但他有一個獨特的學術背景:法律學位、社會理論博士學位,還曾師從德國哲學家哈伯馬斯。
恰好正是這段經歷不僅為 Palantir 的技術核心注入了哲學基因,舉例來說,Palantir 的關鍵技術 ontology,正是出自哲學,研究存在的概念,包含如何把實體分組到基本類別、這些實體哪些存在於最基本的級別的問題。
這也讓他成為矽谷少數哲學背景的科技公司執行長,他的背景也讓他不會對工程師等人進行微觀管理,反而創造了一種用他們的話來講稱作藝術家空間。
事實證明 Thiel 的眼光是對的。

《科技共和國》這本書在談什麼?
想像一下,當其他科技公司執行長在談論快速行動,打破常規時,Karp 卻在引用德國社會學家韋伯的理論。當別人討論產品市場契合度時,他在思考科技與政治的關係。
在公開場合,Karp 會自豪地提到公司交出誇張的數字,然後對批評者說:「致所有憎恨我們的人,好好享受你們的邪教吧。」(And to all people who hated on us enjoy your cult.)
這種大膽、反主流精神的風格貫穿在《科技共和國》(The Technological Republic)一書中。
這本書特別的地方是,Karp 將他的哲學背景融入在商業思考中,他認為科技公司不應該僅僅追求商業利益,同時應該承擔起維護西方民主價值的責任。
這種信念不僅影響 Palantir 的商業策略,更深深塑造公司的文化基因,尤其是像邪教般的文化。(這也是為什麼他會對批評者說「享受你的邪教」來諷刺他們)
《科技共和國》更像是一份 Karp 寫給想要投身科技領域人才的宣言。他先是批判普遍推崇全球化、消費主義與政治中立的矽谷文化。
他指責這些科技菁英從解決國家級重大挑戰,轉向開發購物網站、照片分享應用程式,以及其他膚淺但利潤豐厚的消費產品,這會導致西方文明正在從內部被掏空。
書中有段能體現 Karp 的想法:「最有能力的一代工程師從未經歷過戰爭或真正的社會動盪。當你可以退縮到建構另一個應用程式的安全感中時,為什麼要冒著朋友不贊同的風險為美軍工作?」
接下來,我們會來介紹 Palantir 如何有哪些重要原則幫助他們建立起獨特的文化?在嘲笑與讚譽的兩極評價中,走出一條反主流之路,並試圖重建一個「科技共和國」。
(這裡需要稍稍打住關於 Karp 的介紹,再寫下去會太長,下期我們會來更深入介紹他的背景和職涯轉折,以及如何面對 Palantir 的道德爭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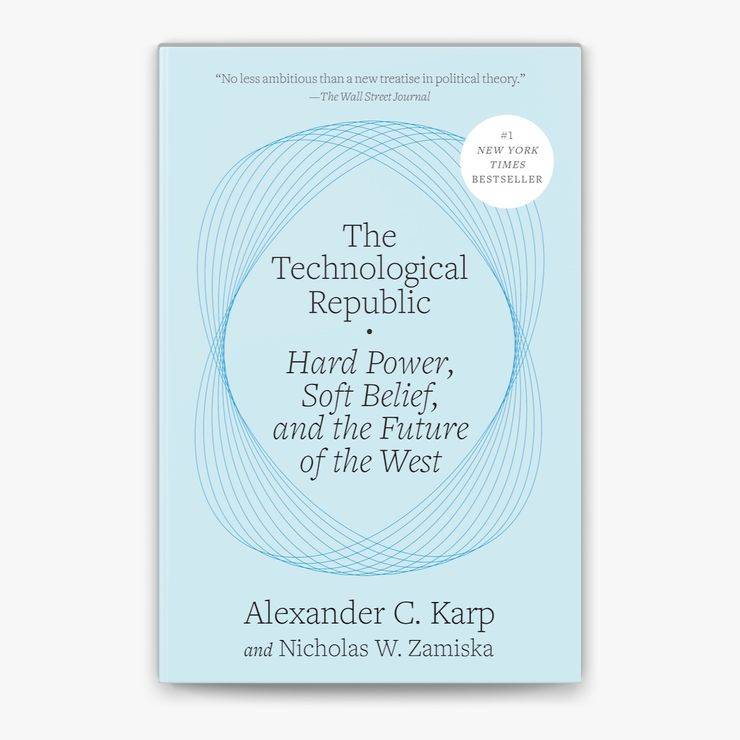
1. 反主流的價值觀:「我們不是矽谷的一部分」
2018 年春天,Google 內部爆發一場前所未有的員工抗議。起因是 Project Maven,一個幫助美軍分析無人機影像的 AI 專案。
數千名員工聯名寫信給執行長 Sundar Pichai:「建立這項技術來協助美國政府進行軍事監控,以及潛在的致命後果是不可接受的。」甚至這起事件有數十人離職,最終 Google 不僅終止該合約,更退出了價值 100 億美元的五角大廈雲端運算標案。
但 Karp 看到的是另一幅景象:一代天才拒絕保衛國家,卻甘願為可口可樂和 Nike 的廣告投放優化演算法。「Google 的員工知道他們反對什麼,但不知道他們支持什麼,」他寫道。「這不是對和平主義的原則性承諾,而是對任何事物的根本性信念放棄。」
Google 的座右銘「Don't be evil」看似高尚(以及後來取代它的「Do the right thing」),但 Karp 認為這是淺薄的虛無主義,這可以從三個部分來解釋:
第一,虛無主義的後果。Google 的核心業務是構建極其複雜且利潤豐厚的機制,用於銷售消費商品的廣告。雖然這項服務至關重要,但 Google(及其大部分員工)卻迴避了國家目的和集體安全等更為核心的議題。
第二,資源錯配的焦慮。當一個社會中最聰明的工程師被吸引去優化廣告點擊率,而非解決國家安全或重大疾病等問題時,整個社會的長期創新能力和競爭力必然會下降。這是一種對智慧資源被浪費在「瑣碎消費產品」上的深切憂慮。
第三,選擇中立的危險。矽谷菁英們的本能是避免採取明確立場、避免選邊站隊、避免疏遠任何人。然而,Karp 認為這會讓一代人陷入持續的準備,卻可能永遠不會參與真正的戰鬥。
這裡可以補充,實際上 Google 在今年 2 月時,已經正式刪除了「不為武器系統開發 AI」的承諾。這項承諾正是因為 7 年前 Project Maven 而出現的承諾。
Karp 明確表示,他的目標是建立世界上最重要的公司。這也使得 Palantir 與矽谷科技公司不同的地方,他們走出一條與眾不同的路:帶有明確的政治色彩。
他們把自己定位為「美國和更廣泛西方世界的劍與盾」。最明顯的案例是他們從成立之初就拒絕在中國和俄國開展業務,因為他們將這兩個國家視為西方的對手。
對 Palantir 來說,更重要的是將企業使命置於利潤追求之上。
2. 深入泥濘、貼近問題核心
Palantir 內部通常有兩種類型工程師,一種是在核心產品團隊(產品開發 - PD)工作的工程師,很少去拜訪客戶;另種則是近期受到大量關注的職位與客戶合作的「前向部署工程師」(Forward Deployed Engineer,以下以 FDE 作為簡稱)。
但有趣的是,在《科技共和國》整本書中都沒有提到 FDE,反而花很多篇幅解釋背後哲學:「貼近問題核心」,任何技術的構建,包括軍事軟體系統,都需要構建者和使用者之間的親密關係,不僅是一種情感上的,通常也是物理上的接近。
先來稍微介紹一下 FDE。他們會直接派駐到客戶現場,深度參與客戶的實際工作流程。每周大約會花到 3-4 天待在客戶的辦公室,比如說:他們可能在 CIA 總部分析情報數據,在五角大樓協助軍事決策,在 FDA 幫助藥物審批,或在金融機構檢測欺詐交易。
前 Palantir 員工 Nabeel S. Qureshi 解釋了,「你需要對困難的產業(製造業、醫療保健、情報、航空航天等)業務流程有深入的了解,然後利用這些知識來設計出能真正解決問題的軟體。接著,產品開發(PD)工程師會將前線部署(FDE)工程師所建立的內容『產品化』,更廣泛地說,是建立能夠幫助 FDE 更好、更快完成工作的軟體。」
FDE 這制度最早的靈感來自 Karp 對法國餐廳的觀察。
他發現在真正的法國餐廳,服務員不只是端菜的,他們是廚房運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了解每道菜的製作方法、食材來源,甚至可以影響菜單設計。同樣,FDE 不只是產品的使用者,而是產品改進的推動力。
在《科技共和國》中,他更詳細解釋當前傳統國防承包商的結構性問題:那些設計陸軍軟體系統的人(包括 Lockheed Martin 的工程師)與軟體的實際使用者(像是戰場士兵、情報分析師)都距離太遠、有嚴重的脫節,這使得使用者和開發者之間的鴻溝已經變得太巨大了。
「貼近問題核心」的核心邏輯,不僅催生出 FDE 的制度,更讓 Palantir 形成幾個重要的行動準則:
打造更好的步槍:Palantir 將工程師直接派駐到阿富汗戰場,與士兵緊密合作,解決他們在對抗簡易爆炸裝置(IEDs)時遇到的實際問題,確保軟體真正實用。這個做法確保軟體不只是理論上可行,而是在戰場環境下真正實用,能夠拯救士兵的生命。
五個為什麼:Palantir 內部廣泛採用「五個為什麼」(Five Whys)根本原因分析法。這種方法體現了他們直面問題本質的文化,拒絕停留在表面現象,而是不斷追問直到找到最深層次的原因。
深入泥濘:工程師不能閉門造車,必須親臨現場,理解現實世界的不完美。因為這些混亂、不完美,揭露了系統的真實狀況,告訴我們哪裡有問題。
這個概念源於美國哲學家 John Dewey 在 1922 年的文章〈實用主義的美國〉中的名言:「必須從高貴的超然中走下來,進入具體事物的泥濘溪流中」 ("get down from noble aloofness into the muddy stream of concrete things")
Karp 認為,這是許多大型專案失敗的根本原因。他們往往在解決想像中的問題,而不是實際存在的問題。他們設計的系統在理論上完美無缺,但在現實中卻無法使用。

3. 避免淪為顧問公司:碎石路、高速公路
在討論 Palantir 這家公司的本質時,通常都會有「這是一家軟體公司還是顧問公司?」的辯論。
會被認為顧問公司也不難理解,幾乎在矽谷的科技公司中,較難看到像是 FDE 這類的職位會跑到客戶現場,深入了解他們的問題,並且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
除了 Karp 對於餐廳和國防產業的觀察有了 FDE 的制度靈感外,真正讓 FDE 落實在組織中的是 Palantir 現任總裁兼技術長 Shyam Sankar。當時他們在服務早期客戶時發現了一大挑戰:如何在公司產品和滿足客戶客製化需求中取得平衡。
Palantir 發現,他們產品在每個客戶現場所需的功能都略有不同。傳統上,這種針對單一客戶進行大量客製化工作被視為服務,公司會希望盡量減少這類工作。
但 Sham Sankar 意識到,為了應對這種差異,他們選擇建立一個平台,而非一個單一、高度垂直化的產品。
身為 Palantir 早期員工 Bob McGrew,並曾任產品與工程團隊負責人,他近期解釋了 Palantir 如何透過 FDE 模式進行產品探索,同時避免讓這項業務淪為純粹的顧問服務。這裡有個關鍵是:區分 FDE 團隊在客戶現場的客製化工作、總部產品團隊的規模性工作。
整個流程可以分成兩部分:
FDE 發現客戶需求後,他們會建立一個「碎石路」(gravel road)的原型解決方案
總部的產品與工程團隊會檢視這個原型,找出可推廣到下十個客戶的通用版本,將其變成「鋪好的高速公路」(paved superhighway)
這確保了 Palantir 既能滿足特定客戶需求(服務),又能建立可擴展的通用平台(產品)。
在第一階段「產品探索階段」,FDE 的職責是彌補產品實際功能與客戶實際需求之間的差距:
解決特定問題,交付成果:FDEs 會與客戶一起工作,解決客戶以前從未解決過的問題。他們承諾交付一個極具價值的成果 (outcome),而不是只是安裝軟體。
建構「碎石路」: FDEs 會到達客戶現場,利用現有產品,填補產品與用戶需求之間的鴻溝。他們會建構一個臨時性的解決方案,Bob McGrew 將此稱為「碎石路」(gravel road),這條路徑將產品引導至目標位置。
以最簡單方式解決: 這種「碎石路」的建造方式,在客戶現場解決一個非常具體的問題時,傾向於採取最簡單的方法來達成目的。這可能是寫一些粗糙而現成的程式碼,因為 FDE 的主要目標是在預定時間內交付成果、解決問題,不需要建立一個可維護多年的軟體。
在第二階段「產品擴展階段」,他們的目標是確保 FDE 在現場的成功經驗能夠轉化為可擴展、可重複使用的平台功能。
尋找通用版本:產品與工程團隊的職責是審視 FDE 建造的「碎石路」。他們必須判斷如何將特定客戶的解決方案應用在接下來的五到十個客戶上。
抽象化思維:產品團隊必須思考比客戶提出的問題更高層次的抽象。他們必須猜測正在解決的「正確問題」,而這個問題往往比客戶最初提出的問題更具通用性。
例如,Palantir 本體論 (ontology) 的發明就是一個案例:與其為每個客戶定義特定的資料庫表格(如人員、金錢),不如建立一個極度通用的資料庫綱要(物件、屬性、媒體和連結),讓 FDE 團隊在客戶現場定義專業化的資訊。轉化為「鋪好的高速公路」:透過這種概括化,產品團隊將「碎石路」轉變為「鋪好的超級公路」 (paved superhighway)。這條鋪好的道路必須不僅適用於最初的原型客戶,還必須適用於接下來的一系列客戶。
FDE 模式有趣的地方在於,試圖從不可規模化找出可以規模化的關鍵。雖然在新的客戶部署初期,公司可能會虧損,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透過不斷的產品探索,產品會變得更適合客戶。
Bob McGrew 也強調,這種模式需要大量的組織紀律,來防止它退化成純粹的顧問業務。包含:專注於「成果」而非安裝、FDE 模式的銷售核心是解決問題的成果價值,而不是軟體安裝或訂閱費。
Palantir 內部有個關鍵指標是產品槓桿是否隨著時間增加,這意味著 FDE 應該能夠利用產品來為客戶交付更多的價值,不需要投入更多的工程師。如果將相同的成果出售給第二個客戶,實施難度應該會大幅降低。
付費內容接續提到:
4. 對抗從眾壓力、建立建設性的不服從文化🔒
5. 借鏡蜂群組織學:去中心化的協作模式🔒
6. 即興戲劇哲學:擁抱不確定性與靈活性🔒
7. 重建科技共和國,跳進創新沙漠中🔒
8.建立所有權、Skin in the game🔒
9. 長期主義:超越季度報告的視野🔒
結論:必須自己發明第三十六房🔒
想知道更多,歡迎訂閱《VK科技閱讀時間》,一個月可以收到 4 篇文章,也能解鎖過往內容,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科技產業故事!
《VK科技閱讀時間》也有 Podcast喔!今天就把 Podcast、YouTube 追蹤起來,我們週三中午更新最新一集!

我們很常聊科技公司故事,但半導體一直不是我的守備範圍。這個領域需要的知識太艱深,光是搞懂晶片、製程等專有名詞,就要花很長時間。
直到看到陳良榕的《胡說科技》電子報。
陳良榕是天下雜誌總主筆,深耕科技報導多年。他不會用艱澀的技術術語,而是用故事和洞察帶你看懂半導體世界。
我很喜歡他用內行者的視角,捕捉被外界忽略的細節。比如從 Google 高層演講中發現連業內人士都沒聽過的「鑽石晶片」技術,或是從博通執行長的對話切入,帶出這位全美最高薪 CEO 如何挑戰輝達護城河。
他不僅分析商業數字,更從人物故事中解讀企業策略,讓你看懂科技巨頭背後的真實競爭邏輯。
《胡說科技》每週中英雙語出刊,目前已有超過一萬多名科技人訂閱,連《晶片戰爭》作者 Chris Miller 也訂閱了英文版。
現在訂閱 3 個月只要 $790(原價 $900),讓你不再只是被動接收資訊,而是能主動理解科技世界的每一個「為什麼」。
👉立即訂閱享優惠: https://bit.ly/47GHw15